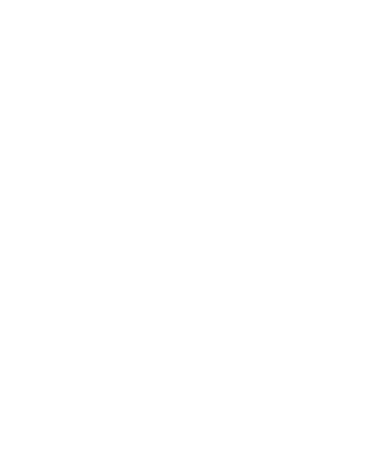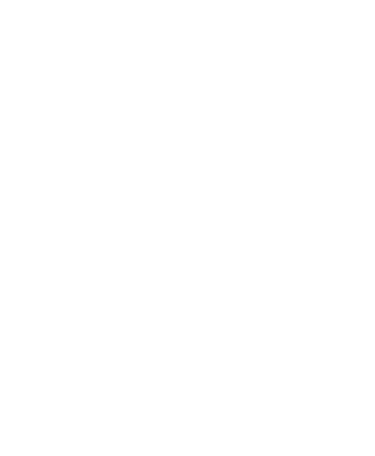殖民时代的延续:日本的东南亚劳工与左派国际主义前景
在全球资本主义对地缘产业的收割加剧之际,左翼当务之急是建立现实的物质联系,促成更具希望的反抗力量。期待日本共产主义组织以更开放的姿态,推动反帝反殖民战线的形成。
DISPATCHJAPAN
Zolaa
6/25/20251 min read
东南亚劳工在日本的处境
跨国劳动力流动是全球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发达国家通过引进外籍劳工填补劳动力市场缺口,以维持国际竞争优势。在新殖民主义框架下,全球供应链的不平等关系建立在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掠夺和经济干预之上。贫困、失业和基础设施匮乏迫使大量人口外流寻求经济机会,却换来低廉的外汇回报和更深层的劳动力剥削。外籍劳工往往被局限在低端制造业、农业或服务业,长期面临不平等的劳动条件、法律保护不足和健康风险。
作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正面临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的严峻挑战,对外籍劳工的依赖逐年加剧。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数据,自2013年以来,外国劳工数量以年均超10%的速度增长。截至2024年底,在日外国劳工总数突破230万,同比增长12.4%,创历史新高。其中,来自越南、中国、印尼和菲律宾的劳工占55%,东南亚劳工更是低端产业的主要劳动力来源。
尽管这些劳工在日本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他们的生存条件却极为艰难,长期遭受压迫与剥削。首先,东南亚劳工多从事农业、建筑、制造业和护理等低技能、高强度工作,工资仅为日本本地工人的60%,约占法定最低工资的80%,且常面临工资拖欠或非法扣款。其次,劳动环境恶劣,建筑和制造业劳工缺乏必要的安全防护,职业伤害甚至死亡事件频发;护理行业劳工则承受超长工时和高强度压力,身心健康堪忧。此外,日本法律对外籍劳工的权益保护不足,语言障碍和法律知识匮乏使其难以维权,许多人因担心失业或遣返而选择沉默。




技能实习制度:现代奴隶制的体现
日本自1993年实施的技能实习制度及相关入国管理条例,是剥夺外籍劳工权益的主要根源。严格来说,日本政府并不承认赴日的东南亚劳工为正式劳动者,而是以“技能实习签证”将其定义为“技术学习者”,限制其在特定地点进行所谓的“技能培训”。表面上,该制度宣称帮助外籍劳工学习先进技术以回馈母国,实则将其视为短期廉价劳动力,加以无情压榨。签证与雇主绑定,劳工无法自由更换工作地点或岗位,稍有反抗便面临遣返威胁。这种制度不仅剥夺了基本劳动权益,还将外籍劳工置于社会边缘。
入国管理条例进一步加剧压迫。特定技能签证虽提供合法工作机会,但居留时间短、申请门槛高,且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劳工难以获得长期居留权或家庭团聚机会,甚至无法享受与本地工人同等的福利待遇。在这一体系下,外籍劳工的生存状态极其脆弱,随时可能因失业、伤病或其他意外陷入困境。
与一些西方国家不同,日本的资本主义体系并未完全拥抱全球化的劳动力市场自由化,而是通过强化地方保守主义,对外籍劳工的流动和权利施加严格限制。这种保守性不仅体现在政府剥夺劳工自由择业的权利,还反映在社会对移民的排斥态度上。技能实习制度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与日本保守主义的妥协:企业通过制度获取廉价劳动力,而保守社会结构确保外籍劳工被隔离于主流社会之外,成为边缘化群体。这种劳动力流动模式,本质上是现代奴隶制与殖民主义的延续,将东南亚劳工束缚于日本经济底层,成为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新奴隶”。
殖民历史的延续
日本与东南亚的劳动关系深刻延续了殖民时期的经济逻辑,体现为以资源掠夺和劳动力剥削为核心的“新殖民主义”。20世纪上半叶,日本通过军事扩张将东南亚纳入“大东亚共荣圈”,强制征用当地劳工开采橡胶、石油等资源,如1942年修建缅甸-暹罗铁路期间,6万名东南亚劳工因恶劣条件死亡。战后,这种掠夺性模式以经济形式重构:日本通过资本输出和技术垄断,继续控制东南亚资源。2022年,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存量达54万亿日元,占该地区外资总额的23%。汽车、电子等产业通过产业链分工,将东南亚锁定在低附加值环节,如泰国80%的汽车零部件出口依赖日企订单,形成依附性产业结构。2023年,日本对东盟贸易顺差达4.2万亿日元,通过高价出口工业品、低价进口原材料,重现殖民时期的单向资源流动。
日本通过经济手段和制度设计,复刻了殖民时期的资源掠夺和劳动力剥削模式。例如,通过官方发展援助(ODA)附加资源条款,如向菲律宾提供港口建设贷款时要求优先供应镍矿(占日本电池原料进口的65%),堪称殖民时代资源特许权的现代翻版。制度性剥削进一步加剧东南亚贫困:印尼劳工赴日需支付约7000美元中介费(约合家庭三年收入),而日本企业通过外劳每年节省超1万亿日元成本。这种财富转移机制与殖民经济中的超额利润提取如出一辙。
面对现代殖民主义,日本左翼的斗争不能仅限于国内组织与宣传。日本资产阶级的权力嵌入东亚-东南亚的剥削网络,其统治依托对地缘经济体系的垂直支配。这种支配通过双重异化实现:将东南亚劳工异化为生产链末端的“非公民化劳动力”,同时将日本无产阶级意识禁锢于“国益优先”的民族主义。在这一虚假对立下,在日东南亚劳工已成为日本社会底层的无产阶级。随着东南亚反殖民斗争的激进化潜力日益显现,日本左翼亟需建立新世纪的国际主义联盟。
在日东南亚劳工多从事农业、建筑、制造业和护理等低技能、高强度工作
受到虐待的在日外籍劳工。


政治潜能与日本左派的困境
日本社会普遍缺乏政治热情,这与其战后资本主义分配关系中被经济利益“收买”的性质密切相关。高速经济增长和福利制度催生了以稳定为核心的保守心态,使市民对政治变革缺乏动力。相比之下,在日东南亚劳工因系统性剥削和压迫,具备潜在的激进性。恶劣的劳动条件、低工资及签证制度的不稳定性催生了他们的政治意识,但经济依赖和遣返恐惧使其难以组织化表达诉求。日本的移民政策和劳动制度实质上压制了劳工的集体行动能力,导致其政治潜能未能有效释放。
日本左翼曾尝试通过多种方式介入劳工问题。“入管斗争”是重要策略,针对日本移民政策中对外籍劳工的压制性规定,特别是对“非法滞留者”的拘留和驱逐问题。左翼团体通过抗议、法律援助和舆论宣传,揭露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的不公待遇。部分团体还为劳工提供签证咨询、法律诉讼和语言培训,缓解其困境。但受资源和规模限制,这些努力影响有限,未能形成广泛的劳工组织化运动。此外,劳工群体的分散性和对风险的恐惧,使其在集体行动中持观望态度,左翼援助多停留于个案层面,难以推动系统性变革。
在跨国层面,日本共产主义组织尝试建立团结关系。例如,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核派)与韩国民主劳总(KCTU)自2003年起合作,联合举办罢工和示威活动。共产主义者同盟委员会(统一派)通过亚洲共同行动和人民斗争国际联盟(ILPS),与韩国、中国台湾、菲律宾的反帝力量保持联系。然而,这些合作多为象征性声援,实际效果有限,未能充分组织劳工或利用其政治动能。在日本资产阶级将利益嵌入东南亚的背景下,日本社会主义革命的未来与东亚-东南亚反殖民力量的发展密不可分。跨国合作虽迈出重要一步,但需进一步深化协作机制,将意识形态整合与物质资源协调相结合,为联合行动奠定基础。
新世纪的国际主义:抵达行动
历史上,跨国劳工的流动性和在地分布使其成为革命斗争的重要力量。共产主义者可利用其跨境优势,高效传递信息和物资。劳工的经济需求和跨国网络的资源流动性,使其成为资金、设备等物资传递的理想媒介。他们的频繁出入境和日常行李携带行为难以引起国家机器的特别关注,为传递革命宣传材料和情报提供了天然掩护。通过这种流动性,共产主义者可建立高效、安全的信息传递网络,规避资产阶级国家的严密监控。
然而,仅依靠劳工的流动性和物资传递能力不足以构建完善的地下网络,还需坚实的群众基础和地区性节点支撑。日本共产主义团体通过高校和工会的“细胞”式组织,或伪装为NGO的据点,需培养更多具备政治潜力的成员。设立表面去政治化的基金会或市民团体,为劳工提供法律援助、语言培训和生活支持,不仅改善其生存条件,还为先锋队组织接触和培养积极分子提供了机会。通过选拔和教育积极分子,逐步构建纪律化的政治网络。同时,跨国协作是网络运作的关键。日本共产主义者需与东南亚及其他地区的反帝势力建立紧密联系,通过劳工的出入境活动传递战略情报和资金支持。
总而言之,东亚-东南亚地区的反帝、反殖民局势与共产主义组织的协作息息相关。在全球资本主义对地缘产业的收割加剧之际,左翼当务之急是建立现实的物质联系,促成更具希望的反抗力量。期待日本共产主义组织以更开放的姿态,推动反帝反殖民战线的形成。
联络及合作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