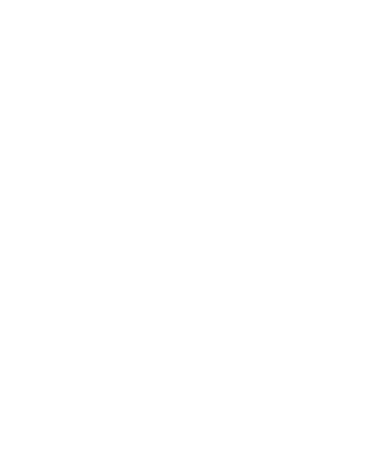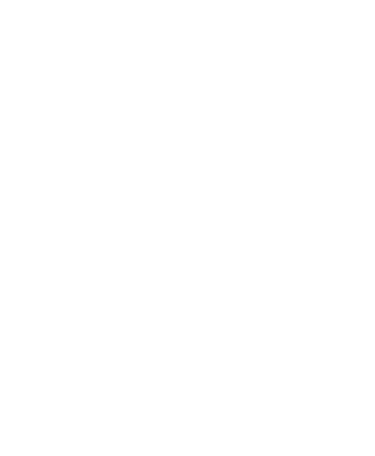《武装起义》(L’Insurrection armée)
序言
LITERATURE & MATERIALS
6/23/20251 min read
序言
出版方认为,这部著作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回应了当前革命无产阶级对这些问题日益增长的兴趣。因此,他们决定迅速出版此书,不再等待作者可能补充或修改的内容。
纽伯格的著作之所以珍贵,主要有两点原因。首先,这是少数由马克思主义者和积极革命者撰写的作品之一,作者曾亲身参与武装斗争,对抗资本主义世界。这是一部严肃的、事实丰富的著作。其次,在当前的历史形势下,这本书具有非凡的现实意义。
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指出:“当统治阶级陷入混乱,群众处于革命激愤状态,中间阶层在犹豫中倾向于加入无产阶级;当群众准备好战斗和牺牲时,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就是直接领导他们向资产阶级国家发起进攻。为此,党要通过宣传逐步强化的过渡性口号(如苏维埃、工人对生产的控制、农民委员会剥夺大地主财产、解除资产阶级武装、武装无产阶级等),并通过组织群众行动来实现。这些群众行动包括:罢工、罢工与示威的结合、罢工与武装示威的结合,最终是与武装起义相结合的总罢工,以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这种最高形式的斗争必须遵循军事艺术的规则,它要求制定进攻行动的战略计划,以及无产阶级的忘我精神和英雄主义。”纲领还特别强调,如果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形势的高潮时刻未能果断发动进攻,“错过起义时机,就是将主动权让给敌人,导致革命失败”。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通过这一纲领的同时,在其政治决议中提到,新的革命浪潮即将到来。一年后的1929年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指出:“自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国际工人阶级明显左倾,工人运动中的新革命浪潮正在逼近。”基于对国际形势的这一判断,全会向整个共产国际及各共产党提出,当前的核心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多数,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组织大规模政治罢工。根据决议,这将“帮助共产党将工人阶级分散的经济斗争统一起来,广泛动员无产阶级群众,并通过引导他们为无产阶级专政直接斗争来丰富其政治经验”。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后的事件完全证实了其结论:这些事件普遍预示着全会决议中提到的时刻即将到来——即为无产阶级专政直接斗争的时刻。
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直接斗争,必然意味着武装斗争,即无产阶级群众的武装起义。根据共产国际纲领,起义必须遵循军事艺术的规则并制定军事计划。然而,随着这一时刻的临近,各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必须为此做好准备,必须研究军事艺术,必须吸取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同时结合本国的具体条件和特点。这一要求自然首先适用于那些革命浪潮进展更快的国家的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如德国、波兰和法国。但在当前形势下,其他国家的党和无产阶级也不能、更不应将武装起义问题的研究推迟到未来。
在本书中,纽伯格仅探讨了起义中涉及军事、战术或技术层面的问题。因此,某些段落会表现出一种“军事倾向”,即对政治因素的阐述不够充分。武装起义是军事艺术的一个特殊分支,因此遵循列宁曾详细指出的特殊规则,这是每位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掌握的。
共产国际纲领总结了无产阶级起义的丰富国际经验,展示了起义如何从普通罢工或示威发展为大规模政治罢工与武装示威的结合。这些国际经验在纲领中以指导形式概括,表明武装起义准备的核心在于党通过罢工将无产阶级群众动员上街,并在此基础上激励和组织他们为夺取政权而斗争。因此,必须重点分析这些因素:它们如何呈现,党如何应对,无产阶级如何反应,事件如何发展,以及从中得出的正反经验对未来有何启示。对于即将到来的时期,这是核心问题。必须向党和无产阶级群众尽可能详细地分析积累的经验,教导他们将罢工和示威提升到更高水平,将其转化为与武装起义相结合的总罢工,以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
在关于军队工作的章节中,对资产阶级军事政策的新变化以及共产党在这方面最新经验的关注不足。
纽伯格写道:“如果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和警察……加上如今各国存在的法西斯武装分队全力对抗革命,即使其他条件有利,革命胜利也将异常艰难。”
纽伯格由此正确得出结论:必须积极开展瓦解资产阶级武装力量的工作。为此,他引用了列宁关于莫斯科起义教训的文章:“如果革命不能吸引群众并波及军队,就谈不上严肃的斗争。”为补充列宁的观点,还需引用同一篇文章的以下内容:“群众必须知道他们正在投身一场武装的、流血的和绝望的斗争。蔑视死亡的精神必须在群众中传播,从而确保胜利。对敌人的进攻必须尽可能坚决;进攻而非防守应是群众的口号;无情消灭敌人是他们的目标;战斗组织应灵活机动;军队中的动摇分子应被卷入积极斗争。”所有革命经验表明,争取军队的工作将在战斗过程中完成,即通过革命群众与军队中动摇且已开始瓦解的分子直接接触实现。这就是列宁所说的对军队的“肉体斗争”,即消灭军官,并根据战后资产阶级军事政策的新变化调整策略。
列宁的这一指示在当前尤为重要。资产阶级新军事政策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其致力于建立政治上可靠的军队。这一现象在所有资产阶级国家中均可观察到,它导致雇佣军和资产阶级志愿军事组织的形成,甚至取代了原有的义务兵役制“国民军”。在许多国家,这一趋势已使得为内战招募的部队成为资产阶级武装力量的核心部分。例如,德国、奥地利和英国(原本无义务兵役制)以及法国(根据新法律,和平时期的军队主要由志愿人员组成)均如此。芬兰的义务兵役制军队仅3万人,而资产阶级志愿组织“舒茨科尔”却有约10万人且装备更精良。
然而,若因此放弃瓦解这些雇佣军的努力,将是严重错误。必须千方百计破坏统治阶级建立绝对服从且可靠的武装力量的企图。尽管任务艰巨,但并非不可能,因为这些资产阶级志愿组织中包含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成分,且不排除派遣革命分子专门渗透以瓦解其组织的可能性。这一任务仅需极大毅力,因为资产阶级对这些部队(其最后防线)的任何动摇或瓦解迹象都极为敏感。
尽管如此,不能指望即使最大胆、最坚韧的工作能争取这些部队的主力支持革命。无产阶级必须预期并准备这些部队“与革命作战”。但另一方面,如果说1923年时无法指望争取国防军和军事警察的较大一部分,这绝不意味着德国无产阶级的胜利被排除。帝国主义国家若彼此开战或对苏联发动战争,仅靠现有的雇佣军或高度训练的法西斯组织远远不够。统治阶级将被迫围绕这些“可靠”部队动员大量工农并武装他们,这将为争取士兵主力创造更有利条件,尤其是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必然引发的革命形势下。但这绝不意味着右倾机会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只能在战后实现的论调是正确的。纽伯格坚决反对这一观点,他正确指出,革命形势的成熟不仅可能由战争引发,也可能在“和平”状态下出现。
早在1906年,当俄国仍实行义务兵役制且有望瓦解军队时,列宁就强调了为争取军队而进行激烈“肉体斗争”的必要性,以及对忠于沙皇的部队发动殊死战斗的必要性。如今,面对雇佣军和法西斯组织,这一点更加重要。必须更加强调无产阶级不仅要提前准备争取军队的斗争,还要准备用武器与之作战,如列宁所说,“无情消灭敌人”。
用什么消灭敌人?如何武装无产阶级,尤其是在瓦解军队的难度日益增加的条件下?
对于1905年革命中无产阶级的武装问题,列宁给出以下建议:“队伍应尽一切可能自行武装(步枪、手枪、炸弹、刀具、棍棒、浸油布条用于纵火、绳索或绳梯、铁锹用于修筑街垒、火药筒、铁丝网、钉子[对付骑兵]等)。绝不能等待外援,一切需自行解决。”(《关于革命军队任务的问题》,1905年10月,载于《列宁文集》第五卷。)
尽管如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拥有比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更完善的镇压手段,但无产阶级也比那时更有条件获取武器。军工、冶金、化工行业的工人接触爆炸物,制造武器,装配炮弹,通过铁路或水路运输这些物资等。
在此条件下,完全可以设想在和平时期对雇佣军和法西斯分队展开一场严肃且胜利的斗争。当然,这只有在其他有利条件下才可能实现,即劳动群众中的决定性分子决心拿起武器,并表现出最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尽一切可能”武装自己。
起义胜利的关键因素不仅是良好的军事和技术准备,还包括群众的战斗意志和牺牲精神,以及一个政治上领导运动并组织运动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存在。在许多情况下,后者甚至起决定性作用。
纽伯格提到,1923年德国仅用几个月就组建了一支25万人的红色卫队,但由于缺乏街垒战术和起义战术知识,这支卫队存在许多不足。尽管德国红色卫队的组织确实存在缺陷,但需警惕机会主义者由此得出的错误结论。起义无产阶级的红色卫队若装备精良且士兵和指挥官熟练掌握军事技能(至少是武器使用、街垒战或野战战术等),将在战斗中取得最大效果并减少损失。但若因等待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红色卫队组建而错过有利的革命形势和政治准备,将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917年2月,俄国无产阶级走上街头推翻专制;同年10月,他们推翻资产阶级时,其武装和军事组织(尤其在2月)众所周知极不完善。但在战斗中(如1923年克拉科夫工人),他们找到了武器、士兵中的盟友以及军事领袖,最终克服内战的种种困难,战胜了装备精良且拥有完整政府机器的敌人。纽伯格将“起义部队对敌人武装力量的军事优势”和“战斗组织介入时群众的参与”列为无产阶级起义胜利的关键因素。实际上,群众参与不仅是起义准备的核心目标,更是其根本目标,其他一切目标必须服从于此。否则,宗派主义或粗陋机会主义的偏差将不可避免。
与此同时 ,我们应当高度肯定纽伯格在书中强调军事技术因素对武装起义准备的重要性。各国共产党内部普遍存在低估这些因素的倾向。无产阶级必须清醒认识到,仅凭热情和决心不足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为此需要武器,需要建立在军事艺术和作战计划基础上的严密军事组织。这正是纽伯格著作的重大价值所在。
关于争取统治阶级武装力量的问题,纽伯格写道:"在军队、海军、警察和宪兵中开展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努力将士兵和水兵吸引到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中来。"
对此需要补充的是,必须仔细区分资产阶级武装力量中不同性质的部队。1905年12月莫斯科起义前张贴在街头的传单就提供了处理这一问题的范例,其中向起义工人提出如下建议:"要清楚区分有意识的敌人与无意识的偶然敌人。消灭前者,宽恕后者。尽可能不要伤害步兵。士兵是人民的子弟,他们不会自愿与人民为敌。是军官和上级指挥官在驱使他们。你们要把打击矛头对准这些军官和指挥官。任何带领士兵屠杀工人的军官都被宣布为人民公敌,不受法律保护,必须毫不留情地处决。对哥萨克不要怜悯。他们手上沾满人民鲜血,历来是工人的死敌。要主动袭击龙骑兵和巡逻队,消灭他们。与警察作战时应这样行动:抓住一切有利时机,消灭所有警官直至警察局长;解除普通巡警武装并逮捕他们,处决其中以残暴和卑劣著称者;对普通警察只需缴械,迫使他们不再为警察效劳,转而服从你们。"
自1905年革命以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有增无减。随着资产阶级国家军事政策的新趋势——将特别可靠的武装分队和内战专用军队与各种形式的全民军事化(包括德国"帝国旗帜"、奥地利"保卫同盟"这类社会法西斯性质的所谓工人军事组织)相结合,这个问题更需要深入研究。
纽伯格的著作对起义中直接瓦解军队的问题,以及争取军队、领导士兵革命行动和组织军队哗变等问题阐述不够充分。相关章节几乎只讨论和平时期的军队工作,且如标题所示,仅涉及共产党的工作,几乎没有谈到无产阶级整体对士兵的影响、劳动群众与士兵的联谊活动、军营与工厂的联系等在任何尖锐斗争中(特别是武装起义时)都极为迫切的问题。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以及苏维埃政权在内战时期的经验,为瓦解军队的工作提供了杰出范例。1919年法国水兵在敖德萨起义的教训,也值得各国共产党认真研究,以便在类似条件下广泛运用。
纽伯格仅在论述党组织军事部门的实际工作和运作时,提到布尔什维克党在武装起义准备中的作用。这些军事部门的良好运作确实是武装起义准备的重要条件,但迄今为止,各国共产党的军事部门普遍未能胜任其任务,且通常缺乏党的充分领导(尽管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中专门要求各共产党开展军队工作)。如果说阐明军事部门的运作是必要的,那么阐明专门负责起义准备和直接领导的机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问题就更为重要。这需要专门章节来讨论,而书中并未涉及。在这方面,首先可以借鉴十月革命的丰富经验。起义的直接准备是无产阶级武装斗争成功的关键因素。这项工作不能像普通参谋任务那样组织,因为它涉及革命武装力量与无产阶级群众及其支持者的联合行动,涉及领导群众武装斗争和政治罢工,涉及协调和指导各群众组织的革命行动,同时要摧毁社会法西斯或纯粹法西斯政党的政治影响,并广泛利用工会(特别是工厂委员会)将无产阶级的局部斗争转变为争取专政的武装斗争。尤其需要通过具体事例表明,一旦起义开始,就必须以不可动摇的坚定性将其推进,无论遇到多大困难。如果共产党当时屈从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的机会主义调和主张,十月革命不知会失败多少次!
必须让党的干部(和无产阶级群众)清楚认识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党组织在职能上的区别。革命军事委员会在起义前夕成立,负责对旧制度发起军事进攻;而党组织则继续开展群众革命动员工作,揭露那些反对武装起义准备的政治敌人。同时,党组织领导参加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共产党员,召回其中表现动摇或无能者,并不断为委员会补充新生力量。
需要特别阐明党在武装起义直接准备中的作用。众所周知,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前几个月就通过群众大会、传单、报纸等渠道,向全体无产阶级公开提出武装起义准备的问题。这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布尔什维克党准备的无产阶级武装起义,绝非布朗基主义式的少数革命者的秘密密谋。军事计划固然需要绝对保密,但在政治上,在准备群众投入武装斗争方面,起义必须在广大无产阶级参与下准备。成功的关键条件,是在群众中传播武装起义思想,使普通工人清楚认识事态发展,理解武装示威和日益频繁的群众政治罢工的意义,明确每个无产者在革命武装力量与统治阶级武装力量交战时的责任。
读者应特别注意书中关于农民群众参与武装起义准备和实施的章节。在这方面,必须充分借鉴苏联和中国游击运动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尤其提供了关于农民革命军队组织结构的宝贵实践指导:1.农民革命军队按地域原则组建;2.每个地区设立受政治领导(共产党或农民联盟委员会)指挥的参谋部,内部设立共产党党团;3.地区参谋部的职能包括:a)通过向全体居民征收特定物资来保障军队供给,b)从老年人中选拔村庄及周边警卫,c)从青年中招募机动分队后备力量,逐步补充到相应作战部队,d)组织军队及周边的侦察勤务,与作战部队保持经常联系;4.农民革命军队组织和作战成功的必要条件包括:a)军队以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成分为主,b)由产业工人和共产党员担任军事政治指挥职务,c)农民行动与城市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相配合。
关于统治阶级的志愿组织,纽伯格引用共产国际六大决议写道:"必须通过揭露这些分队的真实本质,激起群众对他们的强烈仇恨。"这一指示需要发展:不仅要激起仇恨,还要通过一切手段组织斗争,破坏这些分队的活动和存在。在当前的和平时期,阶级斗争实践已经锻造出这样的武器,即无产阶级防卫组织。目前,这些组织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还很不够,因此,更需要尽快就如何在当前条件下对法西斯展开广泛进攻,向它们提供正确指导。
不能同意纽伯格关于巴黎公社、广州起义和1905年莫斯科起义因发生在革命浪潮退潮时,客观上注定失败的观点。这种说法与历史已经证明的马克思主义判断相矛盾。特别是对那些作为革命退潮时期后卫战的起义,必须记住,如果它们成功展开,就可能成为新革命浪潮的起点。
最后,需要讨论关于广州和上海起义的章节。纽伯格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此前未公开的资料,但他对这些运动的解释,与共产国际的路线并不一致。
在描述1927年底广州起义前夕的形势时,纽伯格提到"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涨"等,但在章节结尾,他又写道,共产国际后来认定广州起义是一次后卫战。显然,作者本应首先解释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将广州起义定性为后卫战的决议,并详细说明后卫战的实质。后卫战并非注定失败,正如前文所述,它可能成为斗争新阶段的起点。然而,纽伯格从广州起义是后卫战这一判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广州当时不具备武装起义胜利所必需的,足够成熟的社会条件"。
在论述1927年4月上海起义的章节中,我们遇到多处不准确表述,从中可以推断纽伯格认为:1927年4月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个错误。众所周知,当时共产国际坚决反对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后续事件发展充分证实了这一立场的正确性。纽伯格本应阐明:中国共产党在保持国民党党籍的同时,应当如何行动——即利用在国民党内部的影响力,组建强大的工农革命联盟,领导上海等地群众武装斗争,最终建立工农革命专政。
因此,关于广州起义和上海起义的章节,特别需要读者以批判性眼光仔细审视。
尽管本书存在种种不足,但编辑部确信:阅读此书对每位共产党人、每位革命无产者都将极具裨益。
联络及合作申请
请输入你的电子邮箱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