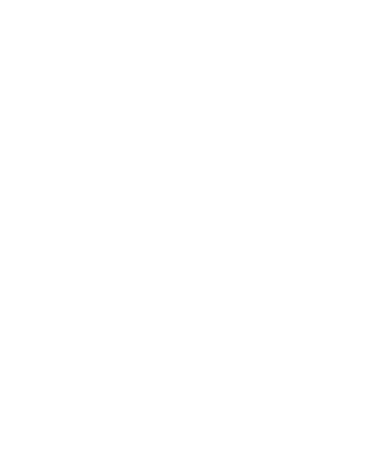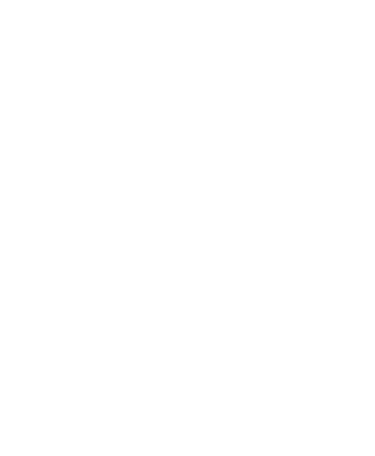资本主义下的阶级与土地变革,印尼土地变革的阶级实质
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虚伪叙事中,有关土地变革问题往往被边缘化,或被局限于对所谓“土地冲突”的表面化讨论,刻意回避其背后深刻的阶级根源。穆赫塔尔·哈比比(Muchtar Habibi)同志在其著作《资本主义下的阶级与土地变革》中,以犀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系统揭示了印尼土地变革的本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农村的渗透、阶级分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剥削与反抗。本篇报道旨在传播哈比比同志的革命性见解,为我们理解并投入印尼及全球南方国家的反帝、反殖、反资本主义斗争提供理论武器。
LITERATURE & MATERIALSINDONESIA
Zolaa
6/23/20251 分钟阅读
印尼的土地问题,长期以来被主流话语简化为资本主义农业公司和采掘业对“农民”土地的掠夺。这种论调看似同情弱者,实则掩盖了农村内部深刻的阶级分化和剥削关系。哈比比同志在其力作《资本主义下的阶级与土地变革》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对土地变革的讨论必须超越这种肤浅的认知,深入到资本主义积累的本质。资本的贪婪不仅仅体现在大型垄断企业对土地的侵吞,更渗透在整个农业生产关系的毛细血管之中。
哈比比同志强调,阶级动态是理解印尼——这个大部分社会生活仍深植于农业关系的国家——土地变革的关键。农业社会的生活图景,本质上是由不同阶级之间的社会关系及其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所决定的。他明确指出:
“如果不关注阶级动态,就无法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农民/小业主之间存在的雇佣关系……这种情况忽视了农业领域有产阶级(资本主义农民和资本主义地主)之间的剥削关系。这些有产阶级凭借其占有的大量生产资料(尤其是土地),得以控制其他社会阶级和工人阶级(本书中称为劳动阶级,即农民兼工人)的劳动力。后者尽管拥有少量土地,但为了维持生计,仍然不得不常年出卖劳动力。”
为了证实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哈比比同志通过对恩琼普朗村(以水稻生产为代表,具有悠久农业生产史)和蒂姆邦村(以棕榈油生产为代表,由移民垦殖形成)的案例分析,揭示了印尼农业社会形态下阶级构成的复杂现实。他将印尼农业阶级划分为三个主要部分:(1)资本家-农民/地主-资本家,他们是农村的剥削阶级;(2)小商品生产者(PCP),他们是摇摆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以及(3)工人阶级,他们是农业生产中的被剥削主体。资本主义地主的存在,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向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过渡的必然产物,他们是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渗透的历史见证。
哈比比同志的分析,有力地驳斥了在印尼土地问题上占据主流的“新民粹主义”思想的虚伪性。这种思想将农民视为一个利益一致的同质实体,刻意模糊阶级界限,从而掩盖了农村内部的剥削与压迫。这种论调,不过是殖民地和后殖民地统治者及其豢养的知识分子所编织的“乡村和谐”神话的延续,其目的是麻痹被压迫阶级的斗争意志。哈比比认为,新民粹主义之所以泛滥,恰恰是因为缺乏坚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传统,以及国家机器在改革后时期公然或隐蔽地支持农业资本主义公司和采掘业对农村土地和空间的疯狂掠夺。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哈比比强调必须具体分析农村社区的历史现实。他指出,在帝国主义中心的国家,农民向工人的转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在被压迫的边缘世界,这一转变主要发生在殖民主义时期,是帝国主义暴力输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当前,边缘世界农业领域资本主义关系的扩张和深化,正是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全球化战略的体现。殖民时期的“原始积累”为后续的资本主义扩张奠定了基础,而近期的资本扩张进程,则进一步加剧了小农的阶级分化,导致他们要么因强制流离失所而被彻底剥夺,要么在更深程度上被卷入资本主义的剥削链条。
针对所谓“土地改革”使农民被驱逐的现象,哈比比认为,不能简单地将其等同于马克思经典意义上的“原始积累”。他指出印尼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其特殊性,原始积累自荷兰殖民帝国主义时期就已经发生,英国模式(原始积累后的大规模无产阶级化)并非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圭臬。印尼的农业生产早已在殖民主义的铁蹄下被迫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农村地区的前资本主义关系已被基于商品关系和市场机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所取代。因此,当前企业对农业用地的掠夺,并非开启“原始积累”,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自身逻辑下的持续扩张和对劳动人民的深化剥削。
哈比比同志同样批判了“半封建”论。这种论调认为印尼乡村生活和农业生产仍处于封建生产关系的掌控之下,这无疑低估了资本主义渗透的深度和广度。虽然某些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可能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得以残存,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方式本身仍是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主导,决定着生产什么以及生产者自身的再生产。
通过对恩琼普朗和蒂姆邦两个村庄阶级动态的深入剖析,哈比比揭示了“农民”这一笼统范畴内部的深刻矛盾。例如,在恩琼普朗,存在着大量“半无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农民”,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依赖与“地主资本家”的利润分成,因为他们自有小块土地的产出远不足以维持生计,必须出卖劳动力。而在棕榈油种植园经济更为发达的蒂姆邦,小商品生产者的境况也与其他地区存在差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官僚政治资本主义农民”这一群体,他们凭借在乡村政权机构中的地位,更有效地服务于资本积累和对劳动人民的控制。
当“资本主义农场主”/“资本主义地主”的利益与工人阶级的利益发生直接冲突时——例如在土地生产力、机械化推广、利润分配、雇工工资、信贷获取等问题上——阶级对立便显露无遗。这种对抗,正是阶级矛盾的体现,并孕育着更为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火种。
哈比比同志的论述,为我们重新审视和推动印尼乃至全球南方国家的土地革命运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它揭示了抛开阶级分析来谈论“农民”问题的欺骗性。所谓“农民”的同质性,只有在将问题局限于国家支持下的大资本掠夺土地时才看似成立,一旦深入到具体的生产关系和阶级构成,这种虚假认知便不攻自破。新民粹主义声称印尼农民总体上是依靠自身劳动维持生计的“小农”,这与哈比比揭示的阶级构成——小商品生产者数量远少于土地匮乏乃至完全没有土地的农业工人阶级——的现实严重不符。
因此,我们必须彻底摒弃这种模糊阶级界限、美化农村现状的新民粹主义农业叙事。取而代之的,必须是植根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深刻揭示农业领域生产生活动态及其背后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革命叙事。
哈比比同志的著作,虽然没有直接为土地斗争制定具体的战略战术,但它指明了斗争的正确方向:必须将组织农村地区的劳动阶级,在他们与农村统治阶级(资本主义农民和地主)的直接生产关系层面展开阶级斗争,置于优先地位。他回顾了印尼农民阵线(BTI)和全印尼劳工组织中心(SOBSI)及其下属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种植园工人联盟(Sarbupri)在历史上的斗争实践,强调了农业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形成独立的阶级意识和政治力量的极端重要性。农村工人阶级长期缺乏斗争经验、阶级觉悟和政治信念,这些不可能凭空产生,唯有通过在自己的阶级组织中进行艰苦卓绝的组织和斗争,才能逐步形成和巩固。
哈比比同志的阐释,是强化印尼及世界各地反抗资本主义压迫运动的理论先声。它以具体、清晰、全面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为我们指明了道路——只有通过组织起来的、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农民的联合斗争,才能最终推翻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剥削秩序,实现真正的土地解放和人民解放。这场斗争,是反帝国主义、反新殖民主义、反资本主义全球大决战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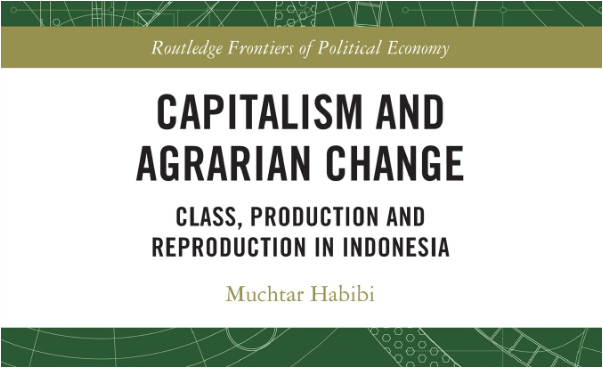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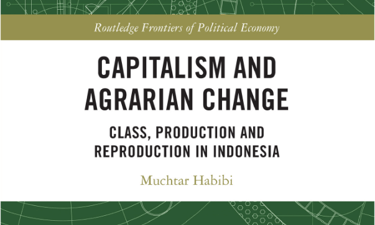
联络及合作申请